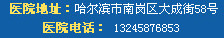绘画的最原始阶段都是单色的,诸如中外都是一样,表现着单纯的明暗和虚实关系。但由于东西方的思想内含的不同,从而在这最本真的绘画处理时,也会形成鲜明的不同风格。
这种单色表现光影的方式,在西方叫做“素描”。他们用炭笔或铅笔,以线条或擦抹的方式控制色阶的过渡层次。看似更为写实,实则每一笔中都有着“人为”明显的痕迹。与西方不同,东方称这种技法为“水墨”,每一笔墨色都不能完全被人所控制。用笔的每丝毫轻重、停留,或是水与墨的配比,这些的系数的精确度都没法与西方素描相比。但中国人却喜欢这样“顺其自然”的意趣,更是将笔墨的戏法上升了无上的艺术。
在这些高级的墨戏中,墨竹的地位可以说是非比寻常。历代的文人都对墨竹情有独钟,明清后,文人信笔而为更重内心感情,对技法之类并没有着重强调。而早期的却更重写实,也就是技法方面会对墨的层次把控较为完美。
宋元间文人画竹,在水墨竹画的起始期就非常成熟了。他们熟练地用墨色的轻重来表现光影与虚实的关系。如北宋的文同与元代的柯九思,他们下笔果断、墨色晕染自然。用重色表现竹叶的前景部分,再在每一组重色竹叶周围用淡墨表现远近虚叶。这种画法与明清的前景与后景分离的表现方法不同。除了竹叶较写实的虚实表现,宋元人画竹也更重“节”。就是在画竹节的时候将竹节用重笔染上一笔,如同梯形的“楔头钉”钉在竹子相连接的两端。这样的手法比明清“勾勒”法的竹节更为细致,也更好地表现出自然深浅的过渡。
“取法乎上,仅得乎中。”艺林堂此套墨竹系列便是将风格定在宋元间。用珐琅彩中的黑料与赭色表现出文人笔下墨色的层次韵味。模仿文同与柯九思,将竹叶与竹节的虚实表现得较为写实。因为材料的不同,我们先用赭色画浅淡的部分,在料还未干之际借助笔力将黑料迅速衔接上。为了更显精细,我们还用极细的线条在竹竿的明暗边缘,绘制出了粗细深浅不同的轮廓线条。
除了细节刻画,连大环境的营造,我们依然是宋元间面貌。竹与竹间倚侧相生,勾连搭配互生姿态。聚密处形成层层叠叠之感,舒朗处似有徐徐清风过境之态。画面正中添置巍峨山石一方,竹林便往后退了一个层次,更有了无限纵深的含蓄意境。
宋元的文人用的是松烟墨,我们用的则是珐琅料彩。虽是不同时间、不同的绘画载体、不同的原料与技法形式,但表现出的却是同一片文脉下的水墨之韵。
在中国“墨色”永远不是单纯指的是黑,而其中包含的色阶、色光、色晕在水墨风格的绘画中表现地活色生香,这种含蓄内敛而又不简单的单色变化中,标榜着我们自己的性格与审美方式。也在信息杂乱的新时代中让我们的文化有着足够的“特性”,从而更好的传承给后世!
01:00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abmjc.com/zcmbyf/8350.html